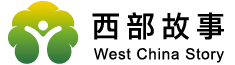家乡年关,风俗习惯是不寻常于别处的。这里不兴盛北疆的红油白菜饺子,也不流行南国的黄糖炒年糕。
熏腊肉。腊月暖阳照耀着一排瓦房,瓦房里灶台前正熏着腊肉,柴火烟雾的笼罩下,竹竿上挂着的一串串五花肉亮锃锃的,焦黄的猪皮上时不时还渗出些许油珠,散发着咸香。挂灯笼。天刚擦亮,全家人背着背篓摸黑在乡间小路上蹒跚前行,年货集市上选了最红最艳丽的灯笼趁着正午前匆匆赶回,在门前丫枝秃条海棠树下置了梯子,爬上爬下——总算“修”完了灯笼这门“必功课”。走亲戚。提前三两天买来糕点屋橱窗里上好的米花果糖,和着今年自家收获的耙耙柑以及水灵灵、甜滋滋的大白菜,携妻带子,摩托、轿车浩浩荡荡“开”进某户山脚人家,夕阳西下,一大家子围在圆桌前品尝主人家的生态菜,这大概是很多地方都有的。

腊肉、香肠
还有一个风俗不知其他地区有不:包年粽子。在中国的传统思想里粽子是端午的代表意向,但在我们家乡经典的过端午的方式是挂艾草和泡澡。相反,没有粽子的新年才是不够体面的年,这一点我是没有记错的。
我的家乡在川西盆地。多雨,湿润。四季树木常绿,不落叶;空气氤氲怡人,气压不低,很舒服。在这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下,各村落田地后的小丘陵上都生了丛丛低矮的粽子粑叶(至少我们这里世代都这么叫它)。粽子粑叶片片鲜腴,饱满。小的像高个子人的巴掌那般长短,大则如前臂长短。这种叶子长得很有辨识点——中间圆两头尖尖,像一艘去了棚顶的画舫,墨绿底色的叶片上错落有致地缀着黄色圆斑,仿佛哪个孩子的荧光棒断了,里面荧光剂一不小心洒出来,落在叶片上闪闪发光。每当年前,老人们就会背着背篓上山割粽子叶,回家用清水细细洗了晾在门口,预备包粽子。
同时,灶台上的大锅里正翻炒着白花花的糯米,加上花椒,清油,红豆和腊肉块,香味简直要溢出来!接下来,全家齐动手,开始包粽子。一下午的功夫,十斤糯米就包完了。

包粽子
晚上,通常是由爷爷煮粽子。巨大的锅里漂浮着一只只碧绿的“小船”。 深夜,粽子的清香缓缓地从锅中溢了出来。我揉了揉惺忪的睡眼,困意顿消,贪婪地嗅着这丝丝、缕缕粽香,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轻轻剥开青绿色的粽叶,真像一个粽子精灵披着一件绿色的棉袄呢!一股粽香味扑鼻而来,露出乳白色的糯米。粽子的馅有肉、豆沙、枣子多种。一口咬下去,这又麻又香的味道充斥着浓浓的家乡年味,直到我心里,使人陶醉。
粽子在家乡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,更是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怀呢!

煮熟的粽子
临近年关。天上,悬着暖暖的冬阳;地上,腊肉、灯笼、粽子将家乡的年装点得喜气洋洋!

天上,悬着暖暖的冬阳;地上,腊肉、灯笼、粽子将家乡的年装点得喜气洋洋!
569 |
0 |
0
总数:0 当前在第1页